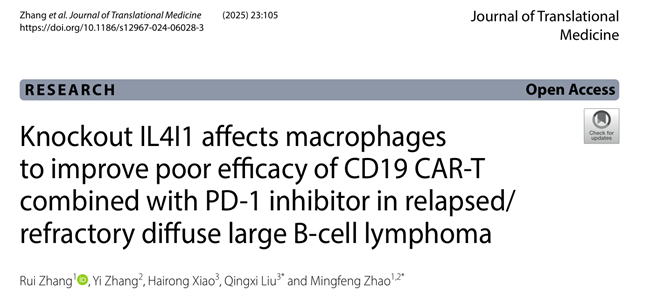逃离,或再生的探险——读《你当像鸟 飞往你的山》
【书与人】
付如初/文
教育和蜕变
对现在的中国读者而言,畅销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最吸引人之处或许不是一个垃圾堆里成长起来的女孩成为剑桥博士的“教育奇迹”,因为大家都清楚,那是“别人家的孩子”,可羡慕不可复制。就像上世纪90年代,我们曾为《哈佛女孩儿刘亦婷》的传奇兴奋不已,而到了今天,我们更看重的是每个人都能学到一两招的《好妈妈胜过好老师》——信息越发达,受教育的机会越多,教育资源的可选择性越强,人们对教育的看重就会越来越理性务实,越来越偏向可借鉴、可转化和可操作——显然,这些都不是塔拉·韦斯特弗的故事能够带给人的,尽管她的英文书名是“受教育”(Educated)。
所以,与其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是一本有关教育的励志书,不如说它是一本有关女孩挣脱被灌输的信仰,借助教育实现自我蜕变的生命之书。塔拉说:“我曾怯懦、崩溃、自我怀疑,内心里有什么东西腐烂了,恶臭熏天。直到我逃离大山,打开另一个世界。那是教育给我的新世界,那是我生命的无限可能。”
这种蜕变,虽然堪称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过程却相当惨烈,身体鲜血淋漓,心灵千疮百孔。她在大山里的自家地下室啜泣的恐惧,和她半夜在剑桥街上的号啕,无法比较哪一个更惨烈。也就是说,这种蜕变或许并不允诺余生幸福,也不允诺自我的妥当安放。然而,生命依然需要这种蜕变,就像所有人明知死亡会到来,依然会生机勃勃地活过一生一样。
对1986年出生的塔拉来说,最刺痛人心的是原生家庭的一切像“原罪”般在她的世界打下烙印,是童年伤痛的总和像宇宙裂变一样不可计数;是爱像不存在一样保持着石头般的沉默,而虐待、忽视、羞辱、伤害则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在这个位于美国爱荷华州山区的家庭里,摩门教的原教旨主义让父亲不相信政府的教育、医疗等所有的公共服务,只相信自然和上帝的赐予,相信生存的一切问题都要靠个人解决。于是,他带领妻子和五个孩子,建立了一个自给自足的“父系氏族部落”,过着一种近乎原始人一般的生活。父亲像一个说一不二的部落酋长,以自己的信仰为所有人的信仰,以自己的意志判定所有人的行为,建立“罪与罚”的秩序。如果不是塔拉现身说法,读者或许很难想象,在21世纪的美国还有这样的角落、还有这样的家庭。不知道在全球化研究者的视野里,这样的个案意味着什么。
这个家庭以收垃圾、整理废品和卖精油为生,于是废品粉碎机的轰鸣伴随着自制精油的古怪味道,弥漫在这个自绝于时代和社会的“部落”里:五个孩子先后被训令不能上学,生病或者发生意外不能求助医院,要随时为世界末日的到来做准备。在这样的训令下,这个家庭的每个成员身上都发生了太多让人不忍直视,甚至有些令人发指的故事:严重车祸、重度烧伤、被废品切割机伤害、暴力虐待,甚至有性虐待的嫌疑等等。神奇的是,居然所有人都挺过了自己的灾难。多年后,全部七个家庭成员分成了两半:三个孩子获得博士学位,另外两个和父母,没有高中文凭,留在大山里。
而自传的作者塔拉,家里最小的孩子,不仅挺过了自己的炼狱,还在哥哥的鼓励下,走出大山,借助外面世界的风煽动自己的翅膀,越飞越高:17岁的她平生第一次走进学校的大门,22岁获文学学士学位,23岁获哲学硕士学位,28岁获剑桥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32岁出版个人自传《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33岁成为《时代周刊》评选的“年度影响力人物”。而此时,她已经有三年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自卑、羞愧、负罪感、怀旧和抱怨、审视、伤痛、裂痕一起,让最亲密的人最隔阂。所以,她才会在书的后记中说:“我已不是当初那个被父亲养大的孩子,但他依然是那个养育了她的父亲”,“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转变,蜕变,虚伪,背叛。而我称之为:教育”。
每个人的成长都是不同程度地离开自己的家庭和父母,这原本自然而然,然而,对塔拉来说,这普通的过程却变成了必须要承受的宿命和苦难,自然,同时也为她孕育了创造奇迹的可能。如果说生命是父母的恩赐,“家庭教育是上帝的旨意”,那生活就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自我教育。
家,是一个公案
对塔拉这样的女孩来说,原生家庭给予的经历是切肤之痛,而经由教育得来的认识是思想翻飞。二者之间总是有巨大的裂痕,也总是纠缠不清,此消彼长。正如乔治·斯坦纳在自己的回忆录《审视后的生命》中,讨论理性遇到非理性和虐待狂的时候说的:“理性是间断出现的天恩,它随时可能碎裂成混乱和荒芜。”所以,尽管教育给了塔拉审视原生家庭和旧日生活的理性,也给了她反思自我、敢于讲述的勇气和能力,但她依然是纠结和挣扎的,就像身上永难消除的伤疤,她无法超越自己的过去。同时,正是这个过去,赋予她的生命独特的意义;也正是家庭和自我的巨大反差,赋予她写自传的资格和意义,让她得以在众多带着原生家庭之痛的孩子中脱颖而出——从心理疗愈的角度而言,讲述是走向健康的第一步。随着她的书在世界各国受到广泛关注,相信她的自我治疗过程也会大大缩短。因为,任何成功都可以归因于补偿性动力,也就是基于自身的不利条件而产生的不断激励自己结果。
从这个角度说,不幸的塔拉又是幸运的。她能够在年轻的时候,完成这样的蜕变和讲述,至少比文学史上著名的另一个“亲子公案”的当事者——卡夫卡幸运得多。
卡夫卡36岁的时候,曾有一封写给父亲的著名的信,讲述自己的“畏父情结”。他说:少年的时候,你是我衡量万物的尺度;之后,你用你强悍的生命力,用外向型的征服性格,不断“恨铁不成钢”,而我,永远都达不到你的要求。于是,性情羸弱的卡夫卡越发感到对生活和自我的无力:他恐婚,无法肯定自己;他退到写作里,写人物的无名、悲催、荒诞。他写约瑟夫·K怎么都难逃审判(《审判》),写K永远无法进入城堡(《城堡》),写格里戈尔变成甲虫就被家庭遗弃(《变形记》)。而在短篇小说《判决》里,情节更荒诞:行将就木的父亲忽然从床上坐起来,“判决”儿子去死,儿子也真的从桥上飞身而下。
跟塔拉的写作充满了生命的动能和改变命运的力量,甚至充满了科学理性的审视和推理不同,卡夫卡的写作一直沉浸在负面的情绪里,阴郁、惆怅、压抑。他生活的时代正是弗洛伊德理论盛行的年代,所以,他的写作通常被认为是精神上“弑父”的举动。然而,这种靠写作完成的“抗争”或者靠“作家中的作家”的不朽声名完成的“自我修复”,丝毫没有带给他任何现世的幸福,40岁时,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家,或者是亲子关系,实在是一个难以回避又永难解决的问题。而每一个时代关注这个话题的角度,都无不指向家庭的诸种问题。即便是简·奥斯汀的年代,人们在为婚姻进行种种努力,看似是将家庭视作未来的安全许诺和希望之所的时候,实际上背后的动力也是要不断逃离原生家庭,重新开始。《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为父母感到的羞愧难以言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范妮要不断忍受父亲的酗酒和母亲的冷漠。只不过,对那个时代的女性而言,离开原生家庭寻找自己的幸福,除了婚姻,别无他途。
所以,塔拉作为21世纪的女孩,又有第二重幸运:尽管出生在严格的摩门教家庭,但至少在大环境上,她是在鼓励个人奋斗和精神成长的美国,因而她对传统的反叛、对信仰的认识,不会背上过多的伦理包袱,反而会更多地被解读为“美国精神”。这种精神,最具体也最抽象,最感性也最理性,最容易崩溃也最可能重建。就像充满暴力和冲突的生活同时也会激发超常的生命活力,痛苦和罪恶中希望之花反而愈加绚烂一样,这种精神充满了悖谬,也充满了哲理。
某种程度上,这种精神也等同于艺术的规律,与同时承受着家庭之痛和作为犹太人的族群之痛的卡夫卡说的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动人心弦的音乐,最美好的歌曲,是由被谴责的灵魂在地狱深渊里完成的——尽管弃绝生活的安宁温暖去获得艺术的成功并非任何生命的本意。生命之所以被诞生是因为它意味着爱和依恋,意味着它天然就应该被尊重。无论在什么时代背景、什么文化环境的亲子关系中,生命“生而自由,且应当保持自由”,都不应该成为乌托邦。没有一种自我是不值得被重视和被改善的。
自我的探险和疑难
华莱士·马丁在《当代叙事学》中认为:自传的写作动机之一,就是自我辩解,或者自我解释,让一个陌生的“我”变成可理解的“我”;跟其他与历史有关的叙事相比,自传因为当事人现身说法,因而显得因果更明确,行动和意图更明显。然而,自传中始终有两个变量不容忽视:一是事情的意义在被回顾时会改变;二是自我在经历这些事情之后也在改变,所以,作者往往会在写作中发现新的意义,也会探索另一个自我。无数的心理学家和哲学家都探讨过,自我不是一个固定的、抽象的同一体,而是感觉、思想和意图的集合体,它变动不居,甚至根本没有可以确认的中心;它既不断被驯化以适应新的伦理模式和生活环境,也不断谋求新的发展,所以它既有各种局限性,又充满了无限可能性。
在《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中,塔拉的“自我”,从萌芽、蒙昧,到成型、清晰,是一条充满了荆棘的小路,觉醒过程也充满了对所有家庭成员的再认识,对家庭这种伦理关系的审视,以及对生命和信仰的新认知。因而在塔拉的“自我”不断成长的时候,我们也得以看到她的所有家庭成员的自我:为了忠于信仰,父亲几乎对所有人的伤痛、血泪视而不见,无论是妻子车祸中的严重脑损伤,还是孩子先后被严重烧伤和被切割机伤害,甚至他自己的严重烧伤,他都是在场者和决策者,但没有一次,他以家人的生命为重;甚至,我们都看不到他对失去其中任何一个家庭成员会产生恐惧。母亲则是完全的服从者,除了对父亲的意志言听计从,读者也很难从她身上看到“母性”——她甚至不记得塔拉的年龄,面对哥哥肖恩对塔拉的伤害和虐待,她无动于衷。
如果人间真的有地狱,或许它就是塔拉在书中描述肖恩被烧成火人,父亲也让他回家自己处理,自己因被肖恩伤害而尖叫,母亲依旧在厨房忙碌的那些时刻。读塔拉的书,经常会让人不寒而栗,也会忍不住想要追问,人到底能够承受多少伤痛?人承受恐惧和伤害的极限在哪里?人的生命力到底有多坚韧?父母的冷漠给人的深渊到底有多深?人自欺欺人的能力有多强?到底有没有上帝?如果有,他在哪儿?靠什么体现对忠于他的弱者的爱?到底什么才是人真正的原罪?该怎么认识来自父母和家庭的爱和伤害?有多少人会以爱之名对最亲近的人实施最暴力的伤害?
尽管塔拉在秉笔直书的时候极尽控制,刻意追求一种科学极简的语言,论文般地“去情绪化”,只表述家庭中所有的事实,甚至她一开始就中正平和地将父亲和哥哥的不寻常表现定位为“双相情感障碍”和“躁郁症”的心理疾病,也尊重所有人对同一事件的回忆,但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情感的涌动,感受到爱恨交织下,一种对另一种温暖可能的强烈诉求,以及这种诉求被压抑后深重的痛楚和疑难。
或许,无论自传写作者实现了什么样的写作诉求,找到了什么样的写作意义,吸引了多少人的目光,生活和经历的真实惨痛都不会因此减弱;而极致伤害一旦发生,再勇敢的人都难以修复爱和信任的记忆,它造成的后果会在往后余生的所有细节中展现出来。或许,我们所有人,一生都难以走出原生家庭的天空。
尽管如此,塔拉在书中几乎没有展现恨意,这也是这本书最让人感动,也最让人震撼之处。身处地狱却不能恨把你推进地狱的人,塔拉面对的是极致的考验,然而,她靠着直觉和天分,靠着自我教育,靠着哥哥泰勒给予的来自音乐和阅读的点滴温暖和光芒,靠着现在的“自我”和过去的“自我”汇聚起来的强悍力量,抵制住了恨和抱怨的诱惑,慢慢朝着相信、善意、松弛和爱的方向努力。所以,塔拉在接受《福布斯杂志》访谈时说的话听上去更像是自我鼓励:“教育应该是思想的拓展,同理心的深化,视野的开阔。它不应该使你的偏见变得更顽固。如果人们受过教育,他们应该变得不那么确定,而不是更确定。他们应该多听,少说,对差异满怀激情,热爱那些不同于他们的想法。”所以,尽管我们不能把这本书当作靠教育获得成功的“励志书”,却可以对教育改变人、塑造人的媒介作用,对教育的方向从知识传授转向深刻认识环境和自我有更深刻的体会。
靠着教育,塔拉尝试进入大山外的世界,努力修复被扭曲的自我;而所有的人,尤其是克服重重障碍接受了教育的“底层人”,都可能会从塔拉的经历中,找到自己的生命方向,寻找自我更新的可能,因为“只有依靠自己,胜算才更大”。
《玻璃城堡》:塔拉式女孩的另一种可能
或许,理解塔拉的书,和理解托尔斯泰的自传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一样,最绕不过去的话题是信仰。她从小最方便接触到的书就是《圣经》,所以,因为读《圣经》,她不仅锻炼了对不懂的东西充满耐心的能力,还将教义的方方面面渗透在对世界和生活的理解中,所以她才会在采访中把《圣经》尊崇为“拥有文学作品所有的一切”,也才会在书中努力秉持爱和宽容的教义。而托尔斯泰尽管在钟鸣鼎食之家,尽管并非纯正的东正教徒,但因父母早逝,自幼缺少爱,所以他早慧,能从更多的角度理解等级和人的差异,理解爱和死亡的关系,理解生活中的挫折和磨难。他从不抱怨,而是不断自我反省。借由省视内心,他保持自己的良知和体恤,也保持了自己写作上的阔大浩荡和人格上的高洁伟岸。
然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关于基督教的信仰总是耳熟不能详的话题,或许因为文化的这种深层隔阂,也无法真正深入内部去了解《圣经》对这些作家的塑造究竟有多大的力量。所以,反而是另一本塔拉式女孩的自传——珍妮特·沃尔斯的《玻璃城堡》,更能让我们产生共鸣,或者能给人更多的关于我们怎么做父母的启发。
珍妮特也是垃圾堆里成长起来的女孩,但她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信仰,而是因为父母的生活理想,他们不想做庸俗的大多数,而是想真正实现自己的理想。父亲心灵手巧,博学多知,幽默风趣,爱心满满。他想要利用自己的物理学知识,在沙漠里找到金子,然后建造一个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但又充分体现物理学原理的“玻璃城堡”。母亲则继承了大片土地和房产,她酷爱阅读,有超常的艺术感觉,立志当一个画家。于是,这样的一家人开始四处流浪,或者是逃亡,理想很美好,但眼前的现实很骨感:基本的生活保障,房租水电,孩子的上学问题等等,常常让父亲焦头烂额——在实现发财梦之前,他需要先去赚小钱。在这个过程中,父亲像理想主义者堂·吉诃德一样,充满了睿智和喜感,也让珍妮特的整本自传充满了幽默和爱。
因为理想不像信仰那么僵化,也因为理想给人的诱惑不像信仰那么虚无,当然也因为他们的生活只是遵从自我选择,而不是生活所迫,所以珍妮特的垃圾堆生活反而充满了特殊安全感,充满了浓浓的诗意和爱。她随着父母的流浪见到了沙漠最不为人知的一面,感受了自然的伟力和壮美;也在母亲影响下,体会了阅读的真正含义,体会了自律和自我选择的真正含义,体会了人与世界的“健康”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她体会了父母不顾一切追求灵魂丰盈的状态。
最后,在见证父母的种种不靠谱之后,珍妮特变成了一个更有责任感的人,形成了最普通的价值观,立志做按部就班工作和生活的“俗人”,但她从父母身上体会到的自由和爱,给了她持久的滋养,也让她从更与众不同的角度定义“家”和“爱”。她借用父亲给她讲的物理学概念,形容家和世界是处在“秩序与混沌的交界”,只要有爱,这秩序和混沌的混杂就不可怕,反而,会有别样的美。而她之所以从垃圾堆里爬出来和父母“决裂”,还能爱和笑,能过正常的生活,是因为她始终不曾失去父亲的爱和母亲的尊重。她知道父亲酗酒、撒谎、异想天开,但她更知道他无条件表扬她的龅牙,不让她自卑;无条件尊重她的选择,不让她难堪。她也知道母亲懒惰、不负责任、不切实际,但她始终没有忘了引导女儿阅读和审美,教女儿自重。于是,他们一家无论在垃圾堆里过着多么不体面的生活,始终都没有失去作为人的精神性的一面,也始终没有忘了幽生活一默。
同样是挣脱原生家庭努力做大多数,塔拉是从生活的背面走来,一路阴云密布;而珍妮特则像是从沙漠的阳光曝晒下努力寻找一丝阴凉,她寻求的只是一种生活的平衡。而如果说塔拉的书最终塑造的是自己的自我,那珍妮特的书,更多呈现的是父母的自我。她成功塑造了父亲母亲的形象,也成功“解释”了自己为何变成现在的“无趣”的自己,一个凡夫俗子:她住着舒适的房子,坐着私家车,路上碰到母亲正在翻垃圾桶找吃的,住在流浪者的安置房里,她拒绝留在自己继承的大房子里,拒绝卖掉自己的大片土地,更拒绝为了女儿的体面而改变自己,而女儿最终也放弃了用物质的方式“孝敬”父母。
显然,《玻璃城堡》和珍妮特的另一本书,写自己母亲成长历程的《半驯之马》,也跟《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一样,是超常的,是溢出普通人生活之外的,更有戏剧性和传奇性的生活。只不过,这种超常更可亲、更松弛,也更让人温暖,更切近读者的感受。跟塔拉的书沉重而严肃的提醒不一样,它幽默而温和地提醒我们:只要给予爱和尊重,亲子关系,或者世上所有的关系,都可以缓解紧张,变得轻松舒缓起来。只是,塔拉的紧张并非出自她的选择,是运气,或者上帝,塑造了不同的命运。
据报道,《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的英文出自《圣经·诗篇》,本身有双重解释,一种是“逃离”,一种是“找到新的信仰”。不知道充满了紧张感和压抑感、还在思念父母和不能回到旧环境中去犹豫纠结的塔拉,让人心疼也让人敬重的塔拉,经由自传的写作和成功,能不能实现“找到新信仰”的愿望,至少她的思考已经接近了这个愿望:
“我很喜欢来自《圣经》的一句话:‘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仰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它让人们相信存在更好的世界,不同的世界,相信我们可以过上与以往不同的另一种生活,体会你从未体会过的爱。但要舍弃过往,想象未来,则需要信仰和教育相结合。只有二者相辅相成,才能遇见未知的人生,期待不一样的改变。”